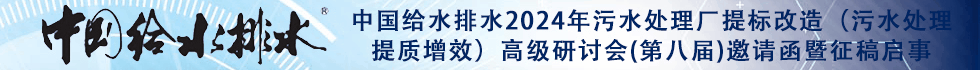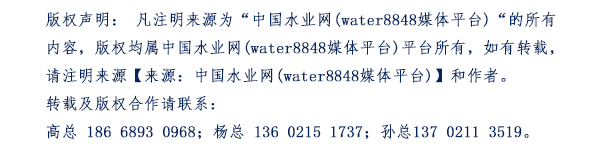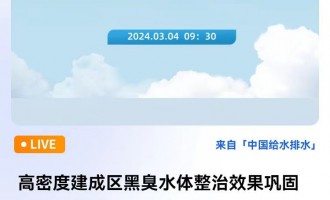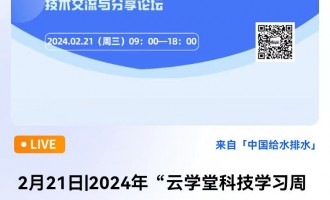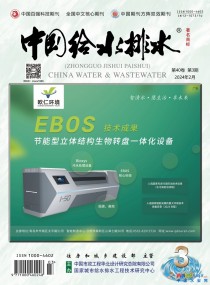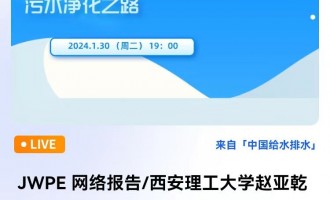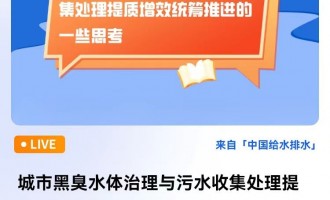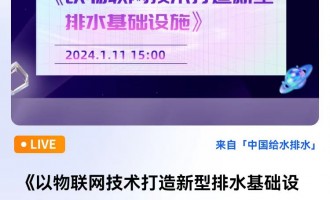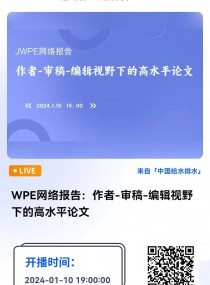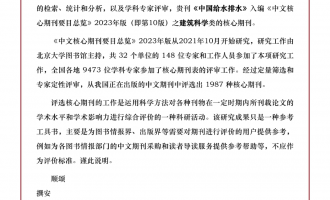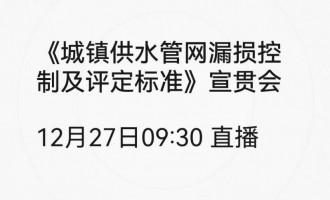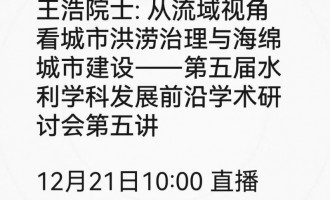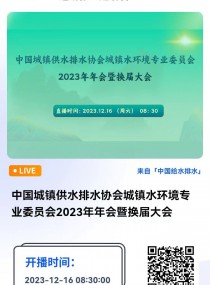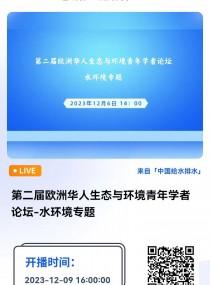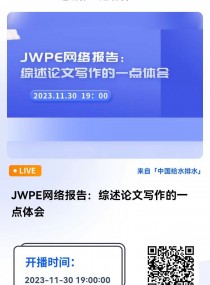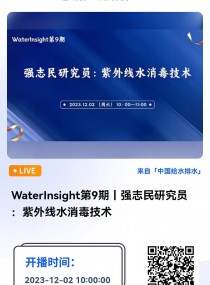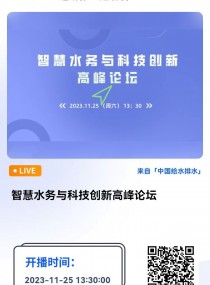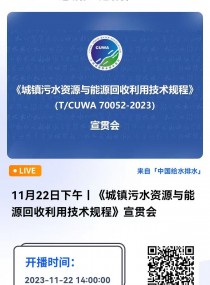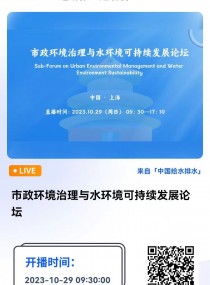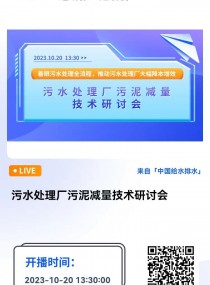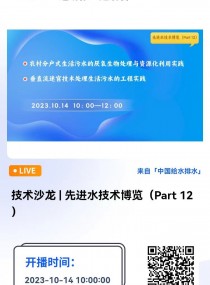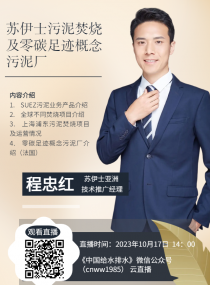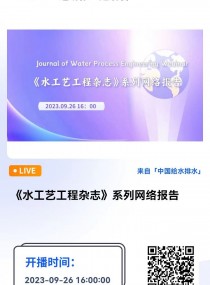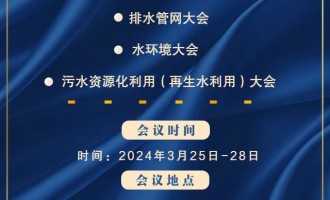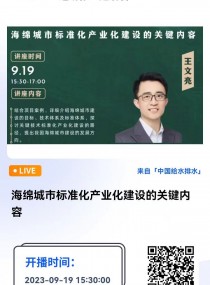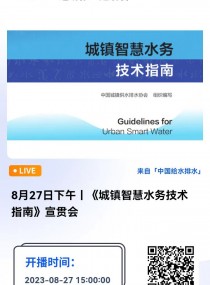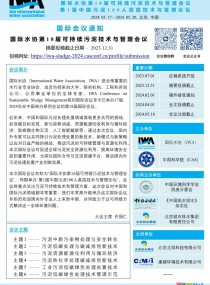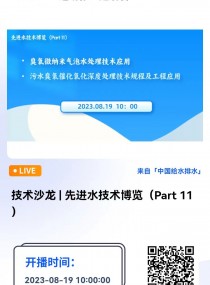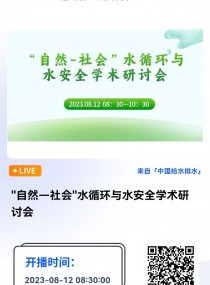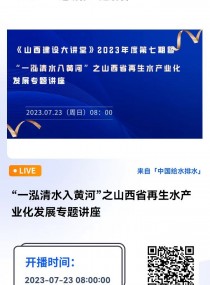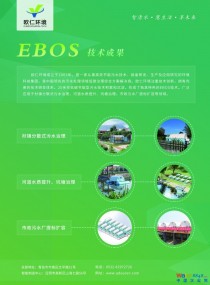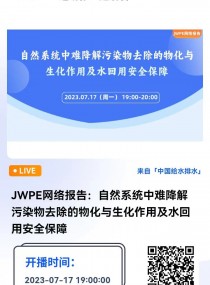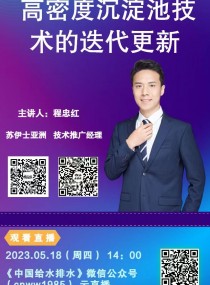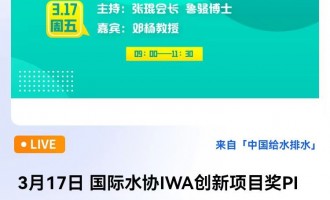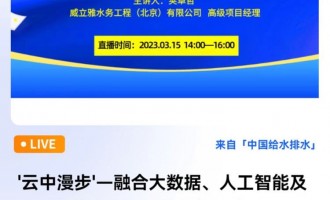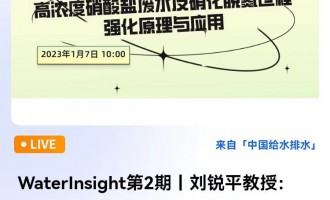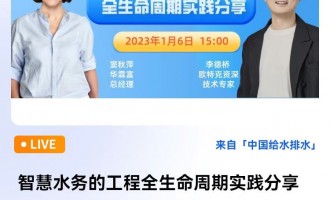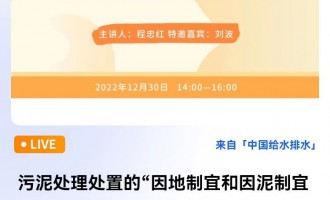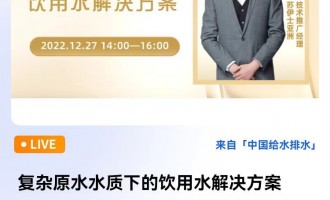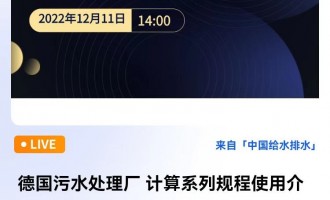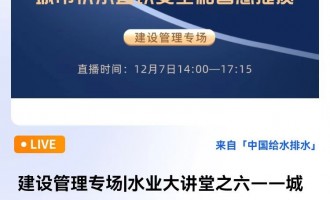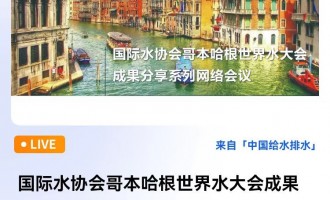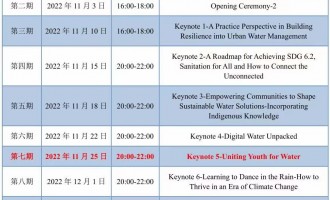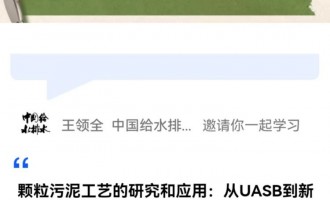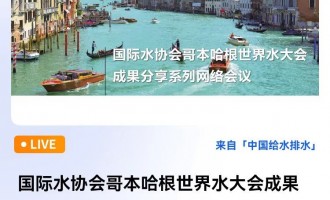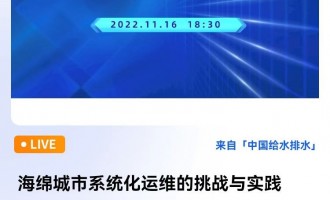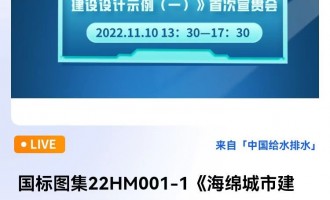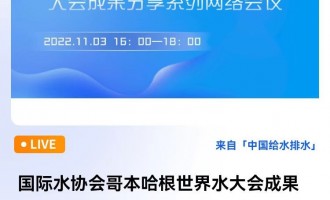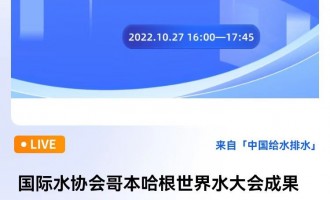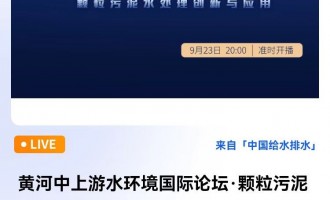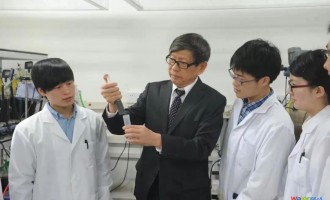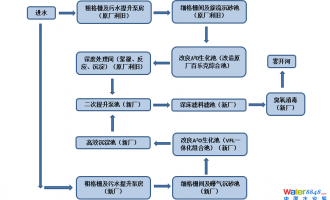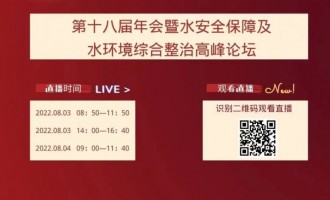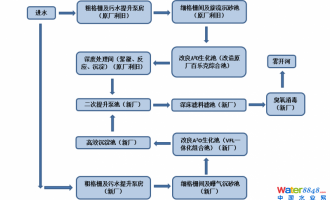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出廠污泥在污染物性質認定上,如果部分重金屬標準未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或十倍以上,不能以“含重金屬的污染物”認定為“有毒物質”。即便污泥屬于工業固體廢物,也不宜直接認定為“其他有害物質”。對涉及案件定罪量刑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意見具有不可替代性,檢測、監測報告僅具有間接輔助作用。對污染物無害化處理的費用不應包括在“公私財產損失”。

【案情簡介】
2010年9月至2018年2月,某市國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產生的污泥由恒順公司運輸處置,期間被告人李某在明知污泥中含有汞、鎘等重金屬的情況下,指使運輸人員將污泥運輸、傾倒至公司廠房及周邊農田土地晾曬。隨著市區污泥量逐年增加,超過了恒順公司生產、加工能力,致使2萬余立方米濕污泥未采取防雨、防流失、防滲透措施,露天堆放在恒順公司廠區周邊田地上。經當地生態環保局認定,現場堆放的污泥為有害物質。為防止污染進一步擴大,當地政府對恒順公司違法傾倒的污泥進行處置。經當地環保局認定對傾倒、堆放污泥處置的必要合理費用為434余萬元,其中濕污泥處置費用420余萬元,評估費用5.5萬元,處置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監測費用8.7萬元。
【控方意見】
公訴機關以污染環境罪提起指控,認為被告人李某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有害物質,后果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并出示以下核心證據支持公訴:
1.某市環保局委托環境監測站出具的地下水監測報告:恒順公司周邊地下水樣品監測,超出III類水質標準0.51倍,其余22項均達到III類標準;
2.某公司出具的土壤監測報告:污泥旁土壤樣品中鎘監測結果達到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值;汞監測結果達到土壤環境質量三級標準值。周邊取樣鎘、汞達到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值。
3.當地生態環保局關于恒順公司非法傾倒、堆放的污水處理廠污泥的認定意見:認定恒順公司非法傾倒、堆放的污水處理廠污泥是工業固體廢物,屬于“有害物質”。
4.當地生態環保局關于未對恒順公司傾倒污泥現場的污泥取樣檢測情況的說明:因國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每年度對污水處理廠的污泥都有抽樣檢測報告,報告中顯示污泥中含有有毒有害重金屬。因而未對現場堆放污水處理廠污泥取樣檢測。
5.污水處理廠委托污泥重金屬含量檢測報告:出廠時對污水處理廠污泥抽檢,含有鎳、汞、銅等重金屬。
6.2005年國家環保總局復函安徽省環保局:污泥應按照工業固體廢物處理。
6.現場勘驗筆錄:未采取防流失、防滲透措施,污泥露天堆放在未防滲的土地上。
【抗辯理由】
被告人提出如下抗辯:
1.從污水處理廠運輸回來的濕污泥雖然含有重金屬,但是重金屬含量很少,使用污泥加工的肥料經檢測結果都是合格的;
2.未對污泥取樣鑒定,無法直接認定污泥屬于“有害物質”;
3.公私財產損失認定錯誤,對污染物無害化處理的費用不應包括在“公私財產損失”的范圍內。
【法律分析】
本案爭議核心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污泥的污染物性質認定;第二,未對現場取樣監測出具鑒定意見是否影響案件核心事實的認定;第三,無害化處理污染物的費用是否納入公私財產損失。
一、關于污泥污染物性質的認定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污染環境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因此,對排放、傾倒以及處置的對象,應限于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以及其他有害物質四類。在本案中,恒順公司處置的污泥為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出廠污泥,不屬于前兩類,但有可能會認定為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
1.污泥屬于有毒物質嗎?
根據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解釋》)第十五條,有毒物質包括:(一)危險廢物,是指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者根據國家規定的危險廢物鑒別標準和鑒別方法認定的,具有危險特性的廢物;(二)《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期德哥爾摩公約》附件所列物質;(三)含重金屬的污染物;(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
《環境解釋》第一條中對含部分重金屬污染物作出超過排放標準“三倍”、“十倍”的界定,從而確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即排放、傾倒、處置含鉛、汞、鎘、鉻、砷、鉈、銻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的、含鎳、銅、鋅、銀、釩、錳、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十倍以上的,應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但是在有毒物質的認定時,究竟重金屬含量達到什么樣的程度能夠算得上“含重金屬的污染物”卻沒有明確的界定,因而無疑給責任人定罪擴大了入罪范圍。
本案中,公訴機關認為出廠時對污水處理廠污泥抽檢,含有鎳、汞、銅等重金屬,可以認定為“含重金屬的污染物”。盡管公訴意見最終是按照有害物質界定,但是強調污泥屬于“含重金屬的污染物”,也足以達到舉輕以明重的效果。司法實踐中,確有將污泥認定為“含重金屬的污染物”屬于有毒物質繼而入罪的案例。詳見【謝水林污染環境案】(2019)皖1802刑初33號。但是,筆者認為既然將“含重金屬的污染物”與危險廢物等并列作為有毒物質的下位概念,就不可能沒有排放標準,而是應當參照《環境解釋》第一條的三倍及十倍標準對“含重金屬的污染物”加以限定。如果重金屬含量并未超標,自然不能認定為有毒物質。本案中的生活污泥在污水處理廠出廠時,即便污泥中含有汞、鎘等重金屬成分,但是如果重金屬含量不超標或者沒有超過排放標準的三倍或十倍,則不應將污泥認定為“有毒物質”。
2.污泥屬于其他有害物質嗎?
根據2019年兩高、公安部、司法部、生態環境部《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環境紀要》)9.關于有害物質的認定。會議認為,辦理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其他有害物質的案件,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污染行為惡劣程度、有害物質危險性毒害性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準確認定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實踐中,常見的有害物質主要有:工業危險廢物以外的其他工業固體廢物;未經處理的生活垃圾;有害大氣污染物、受控消耗臭氧層物質和有害水污染物;在利用和處置過程中必然產生有毒有害物質的其他物質;國務院生態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公布的有毒有害污染名錄中的有關物質等。
盡管《環境紀要》對其他有害物質通過原則+列舉的方式加以界定,但是作為兜底性條款在明確性還是有所欠缺。在沒有明確標準的情況下,基于基本常識、經驗以及歸類就對涉案污染物認定為有害物質,無疑會擴大入罪的范圍。除此之外,《環境紀要》該條規定的另一弊端就在于刻意弱化“有毒物質”和“有害物質”的區別,籠統表述為“有毒有害物質”,這就導致司法實踐中也基本對有毒有害物質不再嚴格區分,只要能夠劃入具體列舉的類別,直接與有毒有害物質等同視之。在本案中,公訴機關直接援引2005年國家環保總局復函安徽省環保局,污泥應按照工業固體廢物處理的結論,作為當地環保機構將污泥認定為有害物質的重要依據。但是,筆者認為污泥屬于工業固體廢物并非意味著就一概認定為有害物質,而是應當結合《環境紀要》的規定,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污染行為惡劣程度、有害物質危險性毒害性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本案中對恒順公司周邊地下水及土壤監測報告,均表明污泥并未對周邊農田土壤及地下水質造成負面影響,表明污泥有害物質的危險性毒害性較小,將污泥不認定為有害物質是有證據支持的。因此,公訴機關提出“污泥=工業固體廢物=有害物質”的論證邏輯是不周延的。
二、關于環境損害鑒定意見的重要性
在環境污染案件中,鑒定意見是基于客觀數據做出的科學判斷,雖然具有主觀性,但是鑒定意見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因而在環境損害案件中具有較強的證明力。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環境損害司法鑒定面臨著鑒定機構數量不足、鑒定成本大、鑒定時間長等現實困難。正基于此,除對污染物性質、定損的專業司法鑒定之外,也在不斷擴展其他類型證據形式。
例如,《環境解釋》第十二條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以及所屬監測機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監測數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第十四條規定,對案件所涉的環境污染專門性問題難以確定的,依照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或者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公安部門指定的機構出具的報告,結合其他證據作出認定。《環境紀要》15.地方生態環境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委托第三方監測機構出具的監測報告,地方生態環境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予以采用的,其實質屬于《環境解釋》第十二條規定的“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監測數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因此,環保部門出具的監測數據、委托第三方監測機構出具的監測報告、以及指定機構出具的報告都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鑒定意見的依賴性。
真正削弱鑒定意見重要性的規定是《環境紀要》14.關于鑒定的問題。會議認為,根據《環境解釋》的規定精神,對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難以確定的,由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實踐中,這類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主要是案件具體適用的定罪量刑標準涉及的專門性問題,比如公私財產損失數額、超過排放標準數倍、污染物性質判斷等。對案件的其他非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或者可鑒定也可不鑒定的專門性問題,一般不委托鑒定。…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難以鑒定或者鑒定費用明顯過高的,司法機關可以結合案件其他證據,并參照生態環境部門意見、專家意見等作出認定。《環境紀要》的本意是確立以鑒定為原則,不鑒定為例外,特別是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難以確定的,應當由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但是司法實踐中,以生態環境部門意見、第三方機構的監測報告代替司法鑒定意見的做法卻越來越普遍。在環境損害案件中,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的費用往往是當地政府部門承擔,這就必然導致主動司法鑒定的積極性不強,在已有生態環境部門意見、監測報告的情況下,司法鑒定被認為多此一舉或成本太高,以環保部門情況說明的方式一筆帶過。
筆者認為,司法鑒定的落腳點就在于出具有證據效力的鑒定意見,而鑒定意見則是在環保部門或第三方委托機構監測、檢測的基礎上由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別、總結而形成的具有科學性的書面意見。鑒定意見的出具需要提取適格檢材、選擇科學鑒定方法,最終得出相對明確的意見結論。因此,在污染環境案件中,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污染物性質、類別、損害等影響案件定罪量刑核心或者關鍵專門性問題作出說明鑒定,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雖然檢測、監測報告等也具有較強的證明力,但卻僅具有間接輔助作用,不可直接替代鑒定意見。
三、關于公私財產損失的認定
根據《環境解釋》第九條的規定,對“公私財產損失”的范圍作出了明確界定,即包括污染環境行為直接造成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以及防止污染擴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產生的費用。在司法實踐中,對《環境解釋》規定的“直接造成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的理解爭議不大,但是對“為防止污染擴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產生的費用”的界定仍有爭議。對污染物進行無害化處理的費用是否應當包括“公私財產損失”的范圍之中存在肯定說和否定說。
1.肯定說。肯定說認為“公私財產損失”是指污染環境行為直接造成的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以及為防止污染擴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產生的費用。包括檢測、評估、清運、處置、修復、補償等費用。因此,對污染物進行無害化處理的費用屬于《環境解釋》規定的“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產生的費用”。
2.否定說。否定說認為,應當參照適用環境保護部《關于開展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若干意見》(環法(2011)60號)所規定的《環境污染損害數額計算推薦方法》,即環境污染損害指環境污染事故和事件造成的各類損害,包括環境污染行為直接造成的區域生態環境功能和自然資源破壞、人身傷亡和財產損毀及其減少的實際價值,也包括為防止污染擴大、污染修復和/或恢復受損生態環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發生的費用,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利益的喪失,污染環境部分或完全恢復前生態環境服務功能的期間損害。因此,按照該意見解釋,傾倒污染物行為所造成的直接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以及因消除污染物造成污染所產生的必要費用,至于污染物本身的無害化處理費用,不能認為包括在“公私財產損失”的范圍之內。
在本案中,污泥處置費用高達420余萬,如果污泥無害化處置的費用從公私財產損失的指控數額中扣除,那么即便構成環境污染罪,但是在量刑幅度上不屬于后果特別嚴重的情形,應在污染環境罪基本犯量刑,對被告人也有適用緩刑的空間。因此,對污泥無害化處理費用是否應當納入“公私財產損失”的范圍對本案被告人的量刑影響巨大。對此,有法官結合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法院(2012)紹刑初字第536號一審判決書歸納審判要旨,認為地方政府在履行環境監督過程中,發現有違規排放、傾倒和處置的危險廢物時,不得不及時進行清運和處置,該部分費用通常也是由地方財政先行承擔。但是在案件已經偵破的前提下,仍可以查清危險廢物的產生者,從而仍可以追究其對危險廢物進行無公害化處理的行政責任。對違規排放、傾倒和處置的危險廢物的無公害化處理的行政責任仍屬于危險廢物的產生者,該部分的行政責任不能因為行為人的犯罪行為而轉嫁給了行為人并讓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即對危險廢物進行無公害化處理的費用仍應當向其產生者進行追繳。對污染物進行無害化處理的費用不應包括在“公私財產損失”的范圍之內。因此,該審判要旨對于本案公私財產損失的認定具有指導意義,應當將污泥處置費用排除出損失范圍。即便將濕污泥運輸處置費用92萬元視為公私財產損失,根據《環保解釋》的定罪量刑標準,不構成后果特別嚴重的情節(造成公私財產損失100萬以上),可在基本犯三年以下量刑,并有機會爭取緩刑。